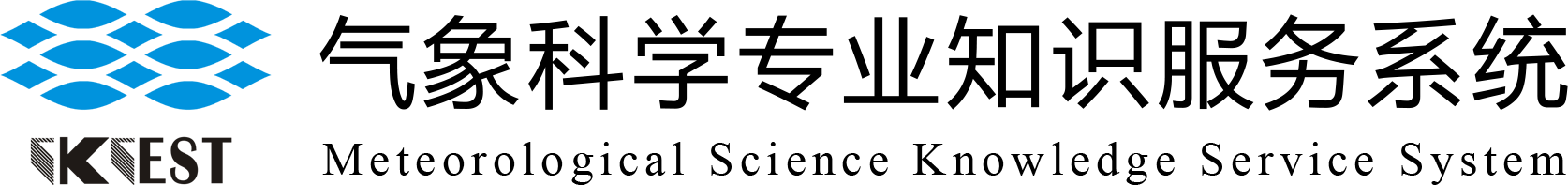“明天会下雪吗?”——这个问题,始于计算,但不止于计算。
要“算”出一场雪,首先得让计算机“看见”大气。现代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将三维大气切割成数以亿计的网格点,每个网格点上都包含着温度、湿度、气压、风向风速等信息。计算机通过求解描述大气运动、热力变化和相态转换等的复杂方程,来推演未来的天气演变。
其中,模拟降水,尤其是雪的预报,核心挑战之一在于刻画云中那些肉眼无法分辨的微观过程。云由无数微小的水汽、液态水滴和固态冰粒子组成,它们通过凝结、蒸发、冻结、融化以及相互碰撞合并不断转化和增长,这些过程统称为云微物理过程。由于这些过程的尺度远小于数值模式的网格,便需要“参数化方案”,即用一套简化的公式来描述这些微观物理过程。
当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开始模拟一场降雪时,它遵循着物理上自洽的规律。首先,在模式计算出的高空低温区,当温度和湿度条件满足特定阈值时,参数化方案会启动冰核化过程,模拟水汽转化为初始冰晶。随后,这些冰晶主要通过凝华、凇附、丛集来增长。然而,它们的命运在落地前仍悬而未决——如果途中遇到高于0℃的暖空气层,雪花便开始融化。最终落到我们手心的是雪、是雨,还是雨夹雪,就取决于这片暖层的温度和厚度,也取决于雪花本身的大小与密度。
有趣的是,不同的云微物理参数化方案,对云内过程的处理各有不同——如对冰晶转化的效率、雪花下落的速度等各种物理过程采用的近似方案、经验公式,都有所差异。因此,有的方案容易算出更多雪,有的则倾向算出雨夹雪。这些细微之别,将直接影响模式对降水落区、强度和相态的预报。因此,在业务预报中,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的输出结果只是一份“初稿”。
此时,预报员的角色至关重要,他们承担着解读和修正这份“初稿”的任务。
首先,是解读天气形势的“大局”。是否有引导冷空气南下的高空槽?槽的深浅和移动速度,决定了冷空气的强度和时机。是否有输送暖湿气流的低空急流?它的位置和强度,决定了水汽的供应是否充沛。而降雪,本质上是冷暖气团一场精确的“邂逅”。它们将在何时、何地相遇?交锋的锋区是陡峭还是平缓?这都将直接影响降水的强度和形态。
再者,是诊断大气层结的细节。其中,从地面到高空的温度、气压的立体配置是锁定具体区域的关键。例如,近地面是否存在会导致雪花融化的“逆温层”?大气整层的温度廓线,是“上冷下冷”的纯雪结构,还是“上冷下暖”易于导致雨雪转换的复杂结构?这些都需要从温压场的垂直剖面中寻找答案。
此时,像探空图这样的工具,便发挥了“临床诊断”的作用。探空图,是由每日定时施放的探空气球观测所得数据绘制而成,描绘了从地面到高空约三十公里范围内温度、湿度、气压和风的垂直分布,是大气层结的真实切片。面对降水相态预报这道难题,预报员会像诊断病情一样仔细审视这张图上的几个关键特征。先是零度层的高度,即气温首次达到0℃的高度。如果这个高度很低,甚至接近地面,那么雪花几乎没有机会融化,降雪概率极大。如果零度层高度适中,比如在几百米到一千米之间,情况就变得复杂。预报员会进一步审视零度层以下暖层的厚度和温度。一个深厚且温暖的近地层很容易将雪花完全化为雨水;而一个浅薄且温度接近零度的近地层,则可能只导致雪花表面略微融化,形成雨夹雪或湿雪。

气象探空图 黄琬婷制图
最后,预报员还需融入对当地地理气候、地形特点、城市热岛效应等的理解。特定地形对气流的抬升或屏障作用,都可能在“最后一公里”影响雪最终落在何处、以何种形态落下。基于此,他们对模式预报进行最终的经验订正。
没有一场雪是轻易“算”出来的。
每一次“明天会下雪吗”的询问背后,都是科学、数据与人类经验共同谱写的答案——这答案,或许预告着一场银装素裹的浪漫邂逅,又或许只是一场潮湿清冷的冬雨。